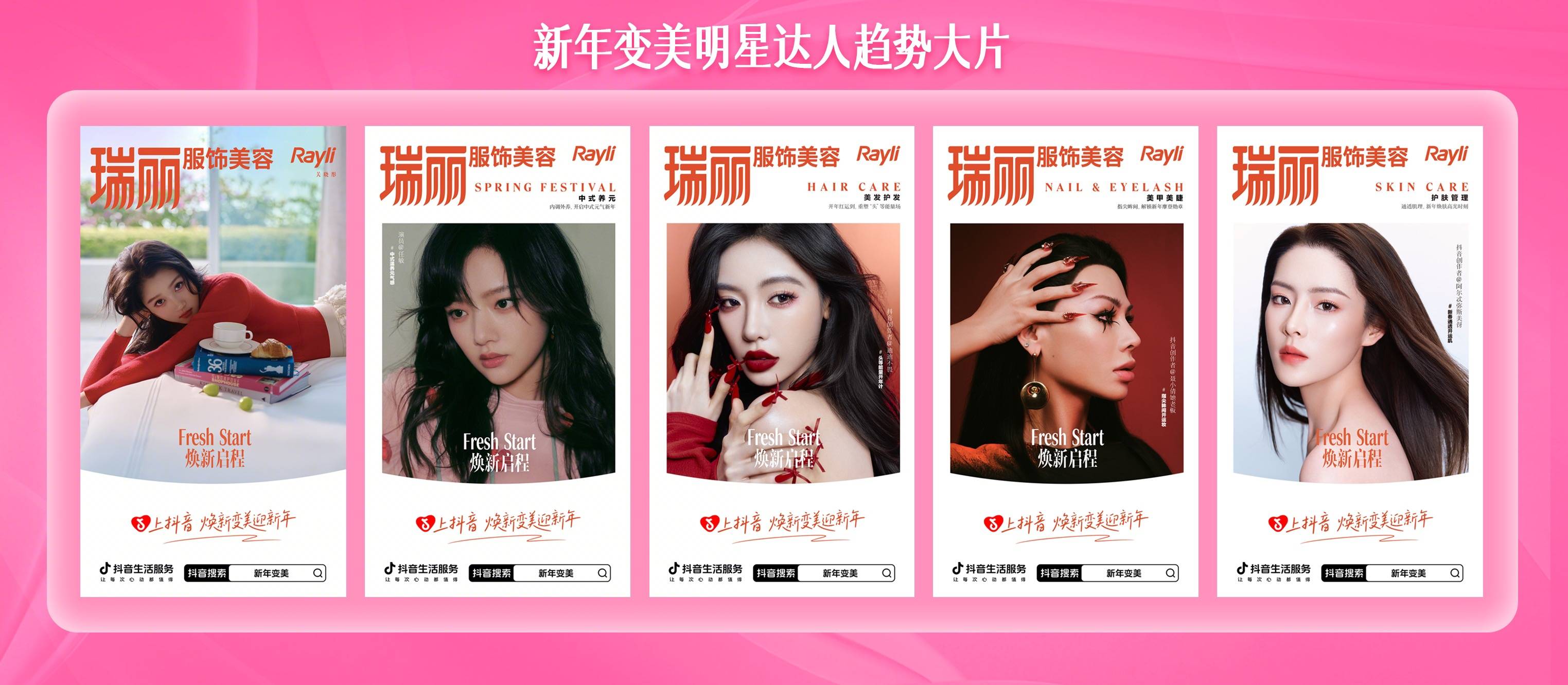陈维扬的电影短片作品 -- 柏拉图的蛋糕 (Plato’s Cake)讲述了关于两个平行宇宙的互动故事:一个男人想要通过穿越到电视另一端去拿取想获得的资源 – 一瓶红酒和一块蛋糕 – 却意外在最后一刻揭露了关于世界的真实走向。从创作雏形直至电影片名,陈维扬深深受到早年在哲学领域上的涉猎和积累影响,造成日后一系列主题的深刻质变;他本人也不讳言,该故事雏形实际启发自伟大哲学家柏拉图的洞穴譬喻,足见古希腊文化的跨界影响力。在故事特色方面,陈维扬始终力求保持一种幽默的荒诞感,以来自不同世界的双胞胎对于有限资源的争夺开始,藉由特殊怀旧的默片形式,再配合35毫米胶片电影摄像机的独特颗粒质感和饱满色彩,带领观众一步步走向故事出人意料的结尾。
如果说,关于一个时代的怀旧情绪,总容易给予人们将世界万物尽数美化的错觉,那些人和事宛若发生在昨日,历历在目,无论能被记得多少,皆避不开以影像作为基本单位的排序与再重组:这或许便是最真实的电影。这世界上,能被人记住的事物是有限的,但人们讲述故事的想像力无限 -- 少有美好,多半伤感,然而对于生于80年代的电影人陈维扬来说,回忆总归都是创作的宝贵养份,理应一视同仁。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我们不难观察到许多人文主义的表徵元素被使用,伴随大量温暖色调的场景渲染,慢慢带领观众回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虚构年代,在如歌诗篇般的花香鸟语中去共情、理解、沉醉、怀旧,却又在最后关头给人一记当头棒喝 -- 这一切彷彿不是典型台湾电影所偏爱的叙事传统及镜头语言;他企图以一种唐吉轲德式的戏谑口吻、近乎陈科滥调的喜剧符号去转化自己想说的答案,同时力求使问题保持开放性,在若有似无间撩拨人的情绪思考,却又坚持点到为止。这样的作品无疑是奇特的,但也令人印象深刻。
回顾亚洲电影传统,尤其在台湾,总有种在“悲情”与“清新”之间持续摇摆不定的题材倾向性,彷彿除此二者之外,没有第三种电影值得拍、值得看。其实,这并不是青年一代导演中缺少说故事的人才,而往往是市场性的考虑,逐渐驯化电影人失去冒险实践精神。谈起改革,属于西方上一代近代文明产物的电影播映技术或许可以提供工具,但真正能够重塑传统的还得是具有更开阔视野的下一代电影人,他们不侷限于一国一地,但能使用同一种语言去讲述崭新的故事。 我们期待更多像陈维扬一样的优秀旅美电影人带来一部接一部的佳作,为未来的观众制造新回忆,也用影像写下想像力的新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