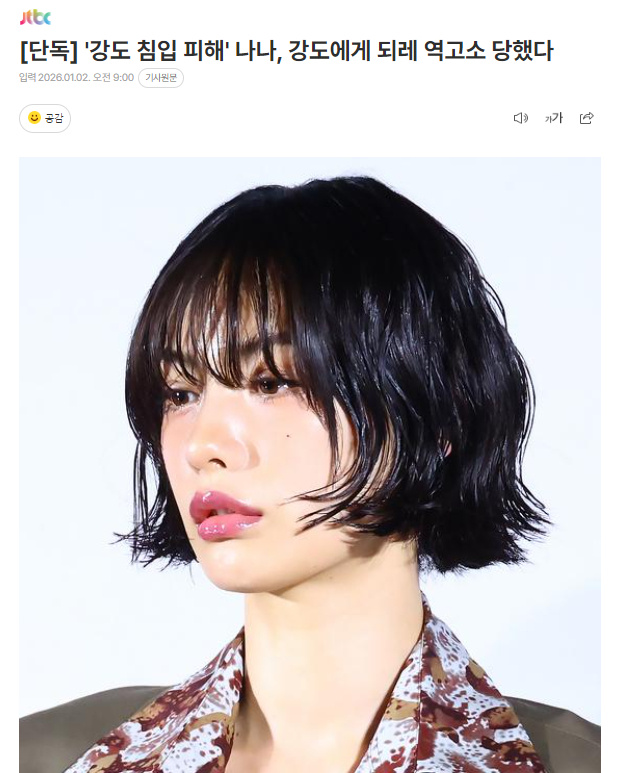“黄浦夺淞”是什么意思?“大上海计划”又是什么?这些多数本地人已经不知其意的名词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上海的命运。上海的命运,远比“小渔村、开埠、改革开放三部曲”这样的描述丰富。
地理塑造了历史,历史又改变着地理。在上海地理这一新开辟的板块中,我们不止步于挖掘历史遗迹,也不简单剖析政策规划带来的城市发展,我们关注的是在这片长江之尾、东海之滨的土地上,每一条街巷、河流和地块里值得继续讲述的过往、人物和事件,我们把这一切都归结为地理,人文地理。
《上海地理》的图卷,从苏州河展开。
河网密布的太湖平原上,曾有两条河流先后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它们携卷着丰沛的太湖湖水一路向东注入东海,两岸的村庄与城镇随着河水的起伏而兴盛衰亡。吴淞江与黄浦江,在历经数百年阡陌交错的河道变迁中发展出各自的使命,前者弱化为一条具有乡土风味的家常河浜,在褪去了工业色彩后日益宁静,而后者成长为一条浩浩荡荡的航运要道,继而孕育出一座在世界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超级港口城市。两条迤逦百余公里的河流在近代交汇于上海,而苏州河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
外白渡桥通常是命运的转折点。剧情片中的闹剧与纠葛在这里开始与结束,而现实中,两条上海最重要的河流在这里泾渭分明。站在桥上向东面望去,远处的黄浦江气势夺人互相推搡着靠近,而桥底流过的苏州河黛眉低拂欲拒还休,两者交汇处喇叭形的河口被一道不起眼的大坝生生隔断。如果稍加演绎,尽可以把外白渡桥下的这一幕发展成痴男怨女的狗血剧情。然而,历史往往比想象更加富有张力,谁能想到在数百年间,黄浦江与苏州河的命运以这样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彼此交织、互相置换,被一步步推向各自的高潮,而上海,不过是两条河流旁的一枚脚注。
上海史学者郑祖安从1980年代便开始研究上海。他关心的是,上海究竟是怎样成为一个大都市的?他在上海社科院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上海近代都市的形成,对他来说,苏州河与黄浦江如同“两条上海的命脉”,他从未放弃对它们的关注。2006年,他出版了《上海历史上的苏州河》,试图澄清人们对苏州河的误会。
郑祖安说,即便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未必厘得清黄浦江与苏州河哪个是母亲河。从今天的现实来看,黄浦江与身畔的东方明珠始终被当做上海的正统地标,而苏州河与娄烨的《苏州河》则固执地被主流之外的声音认可为上海的“底色”。前者长113公里,宽300-700米,将上海分割为浦西和浦东,可以轻易地远眺和辨认;而后者是吴淞江在上海境内的一部分,长54公里,宽40-50米,大多数时候隐匿在弄堂和高墙之内,偏居上海北部“发展中地区”。郑祖安对苏州河的感情更亲近一些,这不仅是因为童年每每骑车在苏州河畔游荡,更因为从学者的角度观看,经历了巨大历史变迁的苏州河与上海的关系更加亲密,而人们却并未重视它的地位。
《尚书·禹贡》里有一句话,“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在古代,广袤的太湖依靠三条大江宣泄入海,娄江、松江与东江。三江之中,尤以中支松江最为宽阔,据《松江旧志》称,唐时河口处宽二十里,宋时青浦县河段尚“面阔九里”。唐时的一里以李世民的双步为尺寸标准,三百步为一里,换算成今天近万米,是可以与长江黄河媲美的大河。这条声势浩大的大江就是后来的吴淞江,因地处吴地得名,其流经上海的部分便是人们所熟知的“苏州河”。而黄浦江彼时只是吴淞江南岸十八浦中一条不起眼的河浜,“尽一矢之力”,一箭可以射到对岸。
不久,娄江与东江便相继淤塞,吴淞江成为太湖主要的泄洪道,同时也是苏州地区的出海航道。在吴淞江下游近海处,一个小渔村悄然发展起来。当地人用一种叫“沪”的捕鱼竹栅捕鱼,因而那附近的江域被称为“沪渎”,这也是上海简称“沪”的由来。小渔村北濒吴淞江,向西可以上溯至太湖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苏州吴县,向东可以通往大海,南面与华亭县城(今上海松江)之间也有极为便利的水运交通。随着太湖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天时地利的小渔村设立海上贸易港口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上海地区第一个对外贸易港青龙镇应运而生。
“青龙镇曾经历过一个辉煌的时代”,郑祖安说,镇上最盛时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放眼望去,街衢井序、烟火万家,“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书法家米芾也曾任过镇监。来自杭州、苏州、湖州的船只每月前来贸易,日本、高丽每年一至,宋朝曾单独设立市舶务,繁华程度时称“小杭州”。倘若不是吴淞江后来的淤塞令青龙镇日渐衰败,上海或许就将在这个繁华了数百年的集镇发展起来。民间尚流传着“先有青龙港,后有上海浦”的俗语,而在今天青浦白鹤镇境内的“旧青浦”,唯有镶嵌于水泥街道中的一排青灰石板路见证了这段久远到几乎让人忘却的历史。
宋代以后,由于长江三角洲的下沉以及泥沙在河口地带大量堆积,吴淞江在海潮的倒灌之下日渐逼仄,大船无法再驶进青龙港。当时的吴淞江水道迂回,泄水不畅,形成了“五里七里一纵浦”的网格化河道,有所谓“五汇四十二湾”之说。譬如白鹤汇到盘龙浦两汇之间步行才十里,河道却迂缓四十里。为治理太湖流域泛滥,吴淞江曾多次裁弯取直,然而河水仍时常漫延过一道道弯,形成新的沼泽和塘浦。
在吴淞江淤积之际,南岸的支流上海浦渐渐成为上海的主要水道,来往的船舶寄锭下锚于今十六铺附近的江岸,一时“人烟浩穰,海舶辐辏”。原本因河流交通而兴起的聚落发展为一座新兴的集镇,南宋末年,上海建镇,标志着官方港口地位的市舶务也从青龙镇迁到了上海镇。然而,上海命运的真正转折此刻尚未发生。
明永乐元年(1403年),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吴淞江流域水患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些河段淤塞甚至已是“茭芦丛生、已成平陆”。户部尚书夏原吉被派去主持治理,正是他彻底颠倒了吴淞江与黄浦江的关系,也从此改变了上海的历史进程。他在《苏松水利疏》中分析认为治水关键是疏浚下游河道,使洪水畅流入海。于是,他开浚范家浜,上接大黄浦,引淀山湖水自吴淞江南跄口入海。范家浜就是如今外白渡桥至复兴岛一段黄浦江,初开时河道阔三十余丈,在上游巨大水量的不断冲刷下扩展到二里许,形成了今天的深水河流黄浦江。从此,太湖水经过黄浦江而入海,而吴淞江在江浦合流后逐渐成为黄浦的支流。这一河道变迁事件史称“黄浦夺淞”,上海就此进入“黄浦水系”,日后轰轰烈烈的上海滩便在黄浦江的润泽下成长起来。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段历史:吴淞江的式微令原本可能孕育上海的青龙镇衰亡,而它的支流黄浦江却在替代了吴淞江泄洪与航运地位后,哺育了上海城。从历史的角度重新考量上海的母亲河,郑祖安会这样回答你:“黄浦江的前身上海浦是吴淞江的支流十八浦中的一浦,因此论辈分,苏州河应是外婆河了。而在黄浦夺淞后,黄浦江成为上海第一大江,上海老城厢是在黄浦江边成长起来的,而不是苏州河边,因此黄浦江与城市的关系更为密切,如同母亲孕育小孩,称黄浦江为母亲河更加妥当。”可以说,苏州河的式微成全了黄浦江,也成全了上海。两条河流带着截然不同的命运相遇在外白渡桥下,哪有比这更传奇、更动人的剧情呢。
苏州河的名字从近代开始刚刚在上海滩流传开来。在为它命名的同时,英国人也赋予了这条河流新的使命。如果说吴淞江仍然让我们想起那条尽管起落不定但自然单纯的古代大江,那么苏州河,这条“通往苏州的河”,则更加暗示了它的贸易航运职能以及这个洋泾浜名字背后的复杂属性。
1843年11月8日,一个叫巴富尔的英国军人带队乘船抵达上海,一周后的11月17日,巴富尔以首任英国驻沪领事的身份宣布上海开埠,由此拉开了上海被动通商的大幕。上海开埠后,日不落帝国的统治者们在划定他们的居留地时,第一眼看中的就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黄金地段。他们在东起黄浦江、西至西藏路、北抵苏州河、南至洋泾浜(现延安东路)的地方画下了一个圈。三条河流围成了天然的屏障,江河交汇的上下夹角濒临吴淞口入海处,为精明的政客和生意人提供了绝佳的方便。而大英帝国领事馆就建立在苏州河河口南岸,面向开阔的江河。
于是,就这么决定了上海的未来。尽管当初这里一片荒凉,唯有大片的农田、密密的芦苇与蒿草,距离老上海的市中心——老城厢一带亦十分偏远,但在资本主义大刀阔斧的开垦下,苏州河与外滩相连的河口成了上海现代城市的源头。英租界设立后,美国人很快在苏州河北岸设立了虹口美租界,与英租界隔桥相望,而法租界则位于洋泾浜以南和老城厢之间。河口位置的两岸迅速集中了美、俄、德、日等各大领事馆。租界的崛起带来大规模的城市化和近代化,使原先中国政府管理的老城厢相形逊色,上海的市中心也由县衙门、城隍庙逐渐转移至南京路和外滩。
正是在这一时期,苏州河被重新定义了。由于英美租界后来合并成为公共租界,苏州河变成了租界区里的内河。比起黄浦江的深阔辽远,苏州河无法形成港区和大工业区,于是渐渐成为居民区和小码头的聚集地。金融、外贸等业务大多集中在外滩沿岸的建筑群内,而由戏院、公园、医院、邮局等构成的外交、文化和生活服务区则自然而然地围绕着浅窄的苏州河展开,形成一条极具西洋风情的观赏性河流。
1855年,苏州河上建起的第一座现代桥梁加速了苏州河口的华丽转身。在此之前,苏州河来回依靠摆渡船,一旦天晚或下雨就无法到达对岸,唯一可以通行的是建于雍正年间的浮桥“新闸桥”,十分不便。英国商人韦尔斯看此契机,在河口头摆渡附近河面建造了一座木桥“苏州河桥”,俗称“韦尔斯桥”。由于韦尔斯桥要收过桥费,引起了民众不满,工部局将其购下拆除,另建一座木桥“公园桥”,因为地处外摆渡,因此称“外摆渡桥”,又因为不要收费,因此它获得了后来远近闻名的新名字“外白渡桥”。外白渡桥建立后,桥上倚栏观景的游客络绎不绝。一批高档的饭店,诸如礼查饭店(浦江饭店)、百老汇大厦(上海大厦)在桥边相继矗立,成为苏州河畔标志性的景致。比起宽阔的黄浦江,苏州河过河更加自然而随意,两岸的隔阂随着一座座桥的建立自然而然消失了,当你走在桥上,会感到桥就是路,两地的大街小巷融为一体。
在天朗气清的日子里,租界区里金发碧眼的外国侨民常常在河边散步,或成群结队地前往附近的地方打野鸭、野兔。星期天,他们会去外白渡桥与乍浦路桥之间的基督教联合礼拜堂新天安堂做礼拜。为了避免黄浦江和苏州河水流对撞形成漩涡和生出浅滩,租界工部局在南口滩地辟建了一个公家花园,夏季的公园里,衣着时髦的洋人常常在河边乘凉、听露天音乐会。而春秋佳日,波涛不惊,河水清澈之时,英国划船俱乐部也常在苏州河上举办赛艇比赛,以为赏心乐事。此后,圆明园路口又建立了上海第一座西式剧场“兰心戏院”,乍浦路桥下的光陆大楼则开办“光陆大戏院”,专演西洋歌剧和放映英美电影。
这些打着年华烙印的旧址成为了如今日渐繁华的城市景观中,令人仰望的“清风明月”。
相比之下,黄浦江畔却是另一种气息。楼盘林立的陆家嘴商圈,矗立在霓虹夜色中几近划破天际的大厦,滨江大道上钢筋水泥铸就的森林,在掩映的灯光中多了几分王家卫镜头中现代都市的冷静与浪漫,近些年来,滨江的老码头边陆续兴起了一些复古与现代风融合的消费场所,临江而建的几处颇有格调的咖啡厅和餐馆,成了这个金融集聚带上的闲暇“绿地”,而滨江码头边上,一家名为诺莱仕游艇会的高端消费场所,也于本月初旬正式营业。
行走在凉风习习的江畔,或斟一杯美酒咖啡倚靠于露台,或乘一艘游艇自在“行走”于浦江之上,追溯历史河流中最初的源头,依然寻觅到主流之外,外滩的“底色”。